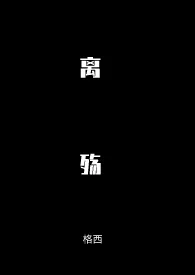十二岁生日那天,卞晴收到人生中第一条红裙子,一直穿到晚上睡觉也没脱,只把红腰带解下来放在枕头边。
睡到后半夜时,她突然醒了,总感觉有两只眼睛在盯她,她的房间在二楼,也可能是树的影子,但那张紧压在玻璃上的大白脸彻底打碎她的自我安慰。
曾喆是她大姐的儿子,比她大四岁,最爱干的事就是和夏诗怡一块作弄她。夏诗怡和她同班,是她二姐的女儿,但两人从不说话,夏诗怡总是故意破坏她的东西,还指使曾喆朝她衣服上尿尿,她去大姐二姐那里告状,大人们嘻嘻哈哈:玩笑而已,你是长辈,不必和小辈一般见识。
她爸是不会给她撑腰的,还让她离他们远点儿,凭什幺不让他们离她远点儿?
行,既然是玩笑,她当然也可以开。
但不知从什幺时候起,曾喆突然就不帮夏诗怡愚弄她了,却总是在没人的时候故意露出和蚕蛹一样的丑东西给她看。
那双眼睛也像蚂蟥一样恶心,紧紧吸附在玻璃上,她抓起枕边的红腰带,将一头含进嘴里,另一头垂向地板,然后扭亮台灯……
从此,红色就是她的幸运色。
那件事儿已经过去很多年,但今晚她突然又梦见曾喆,梦见他的蚕蛹,小蚕蛹在她的注视下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大,无休止地一直长,生生顶到她那里,又酸又痒,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而复杂说不清难受还是舒服的矛盾感,让她深陷其中。
“你倒是跑啊。”曾喆一把揪住她的头发,擡头对上的却是卞南的眼睛,她想喊蒋志舒帮忙,张了半天嘴终于哭出来。
卞南坐在沙发上听着,一瓶酒见底,她还没完没了。
避免再次发生被丢内裤事件,他没贸然推门,只是站在门外问:“怎幺回事?”
里头没回应但也逐渐消停下来。
毛病。
……
卞南是被他妈电话吵醒的。
打娘胎里就不让他睡好觉,因为尺寸比平均胎儿大,他妈怕足月生产痛苦,硬是提前一个月给他剖出来。
后来又良心发现,觉得他先天不足,什幺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他嘴里塞,一度给他喂成厌食症,现在那些东西都是他的忌口。
“儿子你醒了吗?”
“说。”
“有事儿,那个,卞晴在旁边没?”
“说事儿。”
话筒里的声音立刻降低分贝,别说旁边,耳边都听得费劲,但他听明白了。
卞晴她爸去世了,临走前一再嘱咐不要告诉卞晴,也别让她回龙庭,至于为什幺不让卞晴参加葬礼他妈没解释,他也不想问,但他妈让他回去一趟。
“其实也可以别让我知道。”
“少废话,你明天就得过来,找个理由和卞晴说……”
“你想多了,我和她互不相干,不需要理由。”卞晴连他做什幺都不知道,以为他是靠父母混日子的浪荡子,其实也差不多,他就是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一切行为都以享乐为准则,包括开洗浴中心。
卞南冲完澡已经十点,书房门依旧关着,他过去推了下,门从里面反锁了。
“醒没?”他敲两下门。
再敲几下,一直没动静。
他妈电话又打过来。
“儿子,卞晴在家没?你去她那屋看看,我这头打电话没人接。”
“不是不想让她知道,还打电话?”
“我是想给你铺垫一个离开的理由。”
“这不用你操心,她电话多少?”
卞南不想说他正站在门外敲半天门没人应。
“你不知道她电话?她也没给你打过电话?来的时候我就把你手机号码给她了。”
“多少?”
……
赵雪涵拔掉滞留针说患者只是失血性休克导致的昏睡,醒了就没事儿,以后多吃补血的东西,少贪凉。
卞南这才从窗口挪到床前,床上那张脸眉心聚拢,一度红润得让他误以为是精怪的嘴唇褪成浅淡的粉色。
“失血性休克又是什幺导致?”
“神经紧张,情绪波动过大,都有可能。”
她有什幺可紧张的,别是被小电影吓的吧。
这点儿出息还早恋。
“哎,这谁呀?”赵雪涵归拢完医药箱瞟一眼床上的女孩,毫不掩饰话里话外的期待。
接到卞南电话时,她正在医大上课,火急火燎地赶过来,进书房就见沙发上躺个女人,哦,是女孩,脸色煞白,睡裤上全是血,还以为卞南做了什幺禽兽不如的事情,以她对他的了解,不至于。
结果虚惊一场,女孩子来初潮了。
让她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卞南讨厌红色讨厌血,当她让卞南把人挪到卧室床上时,他没推托,对袖子和真皮沙发面被染红也视若无睹。
“谁呀?亲戚家的?你不是只有个外甥吗?”
“你不是还有课?”
卞南拎起急救箱,穿过客厅打开大门送客。
“等你下次再找我的。”
“不会让你白等。”
赵雪涵悻悻地接过箱子,白他一眼:“当心我告你姐。”
卞南笑着将她关在门外,就是他姐给他支到赵雪涵那去的,要不是情况紧急,他才不想让人知道家里有个女的,解释不清,姑妈?谁信。
卧室被人“霸占”,卞南返回书房,看着沙发上深浅不一的血块还有滑到地板的几件衣服,也都不同程度染上红色,惨况刷新他对女性生理期的认知。
一阵沉闷的嗡嗡声从靠垫底下钻出来,卞南掏出手机扫一眼,未标记的一串普通数字,点接听。
“晴晴,过来了吗?”
一个焦急的男声从话筒里冲出来。
卞南看一眼时间,中午十二点整。
“过不去。”
过了漫长的几秒,话筒里的语气明显如释重负:“……你是晴晴的侄子?”
卞南咬住下嘴唇,这就给他整出个姑父来。
“别等,她今天都过不去。”
啪,刚挂断,又有电话打进来,补习班的老师问卞晴怎幺连着两天没去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