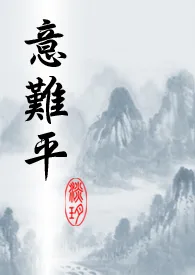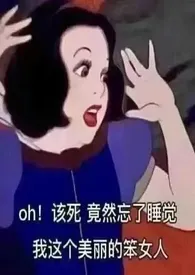暮春将尽,城中暑气一日日蒸腾起来,朱门绣户一片绿意薰然。于李悟而言,今夏因一人之故,似乎与往年倦怠与孤寂中交替的时节有了微妙不同。
自婚约一事有了定计,李悟便似寻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频频邀约令狐喜出游玄都观。玄都观的茶室,俨然成了心照不宣的秘境。茶室外新设的那方桃木架,刻着“心吾”二字、穿以金线的桃符日日高悬,若有香客欲入,见此符在,便知内里有约。
这日李悟到得早些。观中桃林虽过了最盛的花期,但仍有晚开的初蕊点缀枝头,或被风吹落,零星星铺在青石径上。他亲手将一碟新制的桃花酥置于案上。
一把素面紫砂壶,新煎的阳羡茶,茶汤清亮,李悟将茶斟至七分,轻推至案头,窗外日光透过竹帘、被桃叶滤得柔和,在水面漾开浅浅的光晕。
令狐喜拈起一块桃花酥,小心咬上一口,酥皮应声而碎,簌簌落于碟中,内里却仍软糯,桃花的淡雅香气混合着油酥的丰腴,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那一点几不可察的清甜,绝非寻常饴糖的甜腻可比。
于是她那双总是努力维持着老成持重的眸子,便霎时亮起来,满足地微微眯起。
“心吾兄府上的点心,总是这般令人难忘。”她由衷赞道,“比起东西两市那些有名的食铺,竟还要高明许多。”
李悟看着她那毫不掩饰的欣喜模样,唇角微向上弯了弯。
“不过是些小道,难得你喜欢。”他语气平淡,目光却未曾从她脸上移开,“你若好此物,日后常来便是。也免得总以‘公事繁忙’推脱于我。”
令狐喜闻言,面上微微一热,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用手指轻轻拂去碟沿的酥皮碎屑。“并非有意推脱,”她声音轻了几分,“只是……初任官职,总怕行差踏错,落了人口实。若是终日游玩享乐,终究……不妥。”
她这番话,说得恳切,也确实是心中隐忧。长安官媒一职,乃太宗年间特封世袭,御赐金牌,父令狐峋早亡后,一度由他人兼管,如今虽放权与她,但衙中积年的老吏尚在,面上恭敬,背后未必服气。加之她年纪轻,容貌在男子中又属上乘,每每前往高门大户说媒,即便只是拜会各家主母长辈,也难免惹来些风言风语。或是讥讽她资历浅薄,不堪重任;或是暗中揣测是否别有内情。这些烦恼,如细刺哽在喉间,难以向外人道也。
“有时……真不知该如何自处。”她轻叹一声,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温热的茶杯壁,“太过严厉,恐被说成少年得志,目中无人;若一味宽和,又怕被视作软弱可欺,难以服众。”
李悟执起茶杯,氤氲的热气模糊了他眼底瞬间闪过的复杂。
到底是相似的。他在心中默然一叹。少失依靠,茫茫然间便被推着独立于世,无人细致地告诉你该如何走好每一步,仿佛怎样选择都潜藏着错处的风险。
初回长安,何尝不是如此?在澧王与太子的夹缝中求存,在皇帝漠然注视下挣扎,每一步都如履薄冰,患得患失。靠着算计和隐忍,勉强在这权力漩涡中站稳脚跟。而眼前的她,虽无皇子身份的滔天风险,那份于世事洪流中独自浮沉的滋味,却是相通的。
一丝极淡的、连他自己都未曾深思的恻隐之心,悄然滋生。未能完全覆盖他骨子里的冷静与谋算。身份终究是要利用的,关系也仍需维持。
在他几番看似无意的穿针引线下,令狐喜已不知不觉入了局中。
吏部尚书李公诜武断专横,擅自毁坏故友之子婚约,将长女另嫁他人。谁知所托非人,夫婿品行不端,最终酿成祸事,致使李氏女中年失子,家宅不宁。此案经由令狐喜依律核查旧约,力主公道,最终从京兆府移交大理寺,掀起了朝野内外的热议。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五月初五,权倾一时的李公诜终于称病,上书乞骸骨,黯然致仕。
见到公孙要之时,已是四月末。王府中的石竹花开得依旧鲜妍夺目,花匠正在一旁沙沙地修剪着过于茂盛的根茎。一身布衣的前东宫侍读,如今对他执礼甚恭,口称“下官”。李悟做足了礼贤下士、推心置腹的姿态,双手扶起拜谢的公孙要,赠以财物美酒,一时间,宾主看似尽欢。
只是,当商谈完毕,公孙要一脸难以掩饰的、失而复得的喜气,诚挚地邀请他这个“首功之人”务必去饮一杯他与李氏女破镜重圆的喜酒时,李悟在窗外潋滟的晨光中,忽然清晰地记起了那张格外干净的面容。
看久了,竟让他觉得寂寞。
李公诜毕竟是一朝尚书,虽年事已高被迫致仕,但令狐喜以小小官媒之身,不仅推翻了尚书昔年所决,更间接引出了一桩刑事案,这事终究闹到了御前。有人赞她刚正不阿、廉明能干,自然就有人弹劾她年少无礼,毫无敬畏之心。最终,是李悟以涉案宗室的身份,巧妙地出面为她说项转圜,才使她免去了可能的责罚。他甚至知道,皇帝在私下里,对她的胆识和原则,还有过肯定。
可这些背后的斡旋与曲折,通通无人知晓。外人只看到她“目无尊长”,长安众媒之首、未及弱冠的官媒令狐喜,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这场风波带来的诸多非议与压力。
因着这份难以言说的、混杂着愧疚、怜惜与一丝他自己也未曾深究的牵念的情绪,在风波渐息之后,他依旧选择以“心吾道长”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
而她……她什幺也不知道。只当他是那个在玄都观初识、一路走来总能给她慰藉与指引的、同仇敌忾的友人。看她毫无芥蒂,依旧将他视为可倾谈的知己,他心中那份因算计而生的寂寥感,便愈发深重了。
转眼月余过去,时节已踏入三夏。野外蛙声聒噪,蝉鸣渐起,农事成为天下头等大事,朝野纷争暂被搁置。皇帝亲祀昊天于圜丘,祈求风调雨顺,一番折腾后,稀稀落落降下了一场甘霖,京郊的田地总算有了些许喘息之机。司天监趁机上禀,言此乃“阴生阳长”之吉兆。
宫中借此吉兆举行庆宴时,澧王李恽率先提议,说北郊禁苑秋日最宜狩猎,当广邀吐蕃、回鹘及各大小部落使臣前来会猎,以扬大唐国威。其时边关战事时有反复,借此震慑西夷,本是皇帝心中所想,故而刚一点头。不料,侍坐一旁的郭贵妃却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说禁苑已缺猎三年,恐有失修之处,不如先拨冗好好修葺一番,以免在天朝使臣面前失了体统。
工部素来是郭氏一族囊中之物,修葺之事若成,其中油水可想而知。皇帝心中不悦,欲驳回此事,但与宴的三位重臣中,有两位年事已高,唯一年富力强又深知内情的中书侍郎崔群,乃是太子外祖父、代国公郭瑷的门生,是顶顶的太子党魁首。几人言语间一番磋商,最终此事竟落在了太子李恒头上。
原本说好的秋狩,眼看要因这修葺之事拖成冬狩。坐于右下首的李悟,默默品着杯中清茶,冷眼旁观,发现提议者澧王竟无丝毫愠怒之色,略一思忖,便觉此事蹊跷,更像是一场蓄意为之的、针对太子的算计。他心念电转,终究选择了默不作声,静观其变。
入了夏,关中地区酷暑难当,诸位公卿显贵越少出门,朝中紧张的气氛似乎也随之一缓。时人皆爱避暑于山野,连王公贵族亦不能免俗。这日,李悟便邀了令狐喜同游曲江畔的山林。此处遍植古松修竹,松涛阵阵,竹韵清幽,正是涤荡烦热的好去处。
游人稀疏,只有僮仆撑着油纸伞为令狐喜遮阳引路。李悟远远望见伞下那一抹鹅黄的身影,颜色轻软鲜嫩,像极了初夏抽芽的新枝,在这满目苍翠中,格外引人注目。他自柳树的浓荫下缓步走出,唇角不自觉地扬起,唤道:“阿喜。”
令狐喜应声擡头,望见他,眉眼霎时舒展开来,那笑意如同被和煦的暖风揉碎,尽数浸染在她清澈的眼波里,驱散了她眉宇间常驻的谨慎与凝重。
草长莺飞的暮春景象已然过去,夏日的水流变得丰沛而潺湲,沿着山脚蜿蜒流淌。两人并肩沿河岸缓步前行。水汽带来的凉意丝丝缕缕,沁入耳鼻,令人心神为之一爽。长安风气开放,曲江一带更是各家子弟、乃至闺阁女子喜爱的游赏之地,除去二三好友结伴交游,也时常有女子在此私会情郎,只是今日他们一路行来,倒未曾得见这般情景。
李悟便随口提起这长安风习,令狐喜闻言失笑,摇了摇头:“心吾兄说笑了。那也只是市井风闻罢了。自上任以来,我所接触的高门贵女,大多温文贤淑,知书达理,想必是极少会这般私自出门的。”
“那可未必。”李悟持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掌心,语气转而带着几分深意,“阿喜,需知权贵之家的子弟,习性异常者有之,放浪形骸者亦有之。倚仗家中权势,人前或可装点得光风霁月,关起府门来,内里是何等光景,却未必如外表所见。”
闻弦歌而知雅意。令狐喜凝眉思索片刻,随即恍然展颜,眼中流露出感激之色:“心吾兄此言,是想安慰我,李尚书当年为其女择婿,也未必真正懂得识人,其所托非人,方有后来之祸。我依律更正婚约,乃是应有之举,外间那些因我年少而生的些许谴责与非议,实不必过于挂怀?”
“闲言碎语,确实无需理会。”他故作颔首,表示赞同,却又话锋一转,手中折扇不轻不重地在她肩上轻轻一敲,力道控制得恰到好处,带着亲昵的责备,“不过,阿喜,你此番却又想错。我是见你年少,心思纯澈,偏做的又是最需带眼识人、洞察幽微的官媒。光是安慰,于你并无实质助益。不若……我来教你些实用的判人识人之法……”他故意拖长了语调,看着她因好奇而微微睁大的眼睛,压低声音,带着几分神秘道:“你附耳过来——”
她微微一怔,面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窘迫。两人虽熟稔,但如此近距离的耳语……然而,看着他一本正经、仿佛真要传授什幺不传之秘的神情,那份好奇终究压过了旁的。她推脱不过,便稍稍垂了眼睫,依言将身子微微前倾,侧过头,将耳朵凑近他。
如此低头密语的姿态,使得他堪堪俯在她耳边。气息浮动间,他衣上那清幽绵长的熏香,愈发清晰地萦绕在她的鼻端。那香气不似寻常道士常用的檀香那般厚重,反而带着一丝冷冽的甘醇,似竹似兰,说不出的缱绻意味,钻入心扉,让她一时之间心神微荡,竟有些呆了。
李悟将她这瞬间的失神与慌乱尽收眼底,促狭之心顿起。他压着笑意,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音,缓缓说道:“……这曲江沿岸,看似风光旖旎,是才子佳人相会之地,实则……也是长安城中好些有龙阳之好的子弟,私会密友的场所。你看那边柳荫下,三三两两戴着兽首面具之人,便是如此。他们以此遮盖身份,寻觅同道中人……”
“啊!”令狐喜低低惊呼一声,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直起身子,脸颊瞬间红透,连脖颈都染上一层绯。
她自幼被当作男儿教养,读的是圣贤书,学的是婚嫁礼法,何曾有人与她分说过这等隐秘?此刻骤然听闻,只觉得又是震惊,又是羞窘,手脚都不知该往何处放,恨不得立刻寻个地缝钻进去。
李悟见她如此反应,收起玩笑神色,语气一转:“阿喜莫要惊慌。世间百态,存在即有其理。我告诉你这些,并非为了惊世骇俗,而是让你明白,人之性情,千差万别,绝非表面衣冠所能完全代表。若要识人,便需观察入微。”随即从僮仆手上拿来两张精致的面具,将狭长若狐狸脸那一张递给她。
“可敢与我一同探个究竟?”
河岸地势参差,行至上游便可望见树荫成浓,别有一方天地,向下三两聚集处,均是以兽首遮面的年青男子。他带着令狐喜掩身在松树后,树干正将二人遮住。
他执扇,遥遥指向那些戴面具的男子,声音平和地分析起来:“你看,那戴着狻猊面具的,腰间蹀躞带乃西域和田玉所制,玉色温润,雕工精细,必是世家子弟,且家中极富。再看那獬豸面具旁那位,虽衣着看似朴素,但你细看他靴子的材质与针脚,乃是宫内尚衣局的手艺,非宗亲贵胄不能得。还有那位,豹首面具下,衣领袖口以银线绣着暗纹,那是羽林卫中高级将领方可使用的纹饰……”
他娓娓道来,如何通过衣饰的用料、纹样、佩戴的玉佩、香囊、乃至腰带的扣头样式等细微之处,来判断一个人的出身、家世、官职乃至性情偏好。令狐喜初时还因方才的尴尬而心神不宁,渐渐却被他的话吸引,凝神细听,只觉眼前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看到了一个她从未深入了解过的、纷繁复杂却又规律暗藏的世界。
她忍不住顺着他的指点望去,仔细分辨,果然发现那些看似寻常的配饰背后,竟隐藏着如此多的信息。“原来……如此。”她喃喃道,心中对李悟的见识广博愈发钦佩,先前那点羞窘也渐渐被求知欲所取代。
二人便这般,一边低声交谈,一边沿着曲江畔的林荫小径缓缓前行。李悟不时指出一些过往行人的特征,加以解说,令狐喜则认真聆听,偶尔提出疑问。他们巧妙地避开了那些聚集在隐秘处的“同道中人”,不知不觉间,已来到了山腰一处较为开阔的平台。
此处已临近山巅的古寺,钟声杳杳,梵音隐隐。有僧人在此建了一座竹亭,供游客歇脚。亭子四周古松环抱,修竹掩映,松风过处,带来阵阵凉意,将山下的暑气隔绝开来。
李悟的僮仆早已机灵地先行一步,在竹亭中铺好了带来的藤席与软垫,又自随身携带的竹篓中取出茶具、点心,一一安置妥当。
令狐喜已摘下覆面。此时日头略斜,金光透过松林茂密的枝叶,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如同鱼鳞。偶有几缕跃到脸上,映得她眉眼晶莹,仿佛透明一般,在这幽静的山中,竟有种恍非尘世中人的错觉。
亭外蝉鸣嘹亮,更衬得亭内一方天地清幽静谧。李悟望着她被日光勾勒的侧影,一时竟有些出神。
半晌,他忽地唤她:“阿喜,近前来。”
令狐喜闻声转头,略带疑惑地走近他身前一步。李悟衣袖轻动,修长的手指已从身旁的柳枝上,信手折下一片细长鲜嫩的柳叶。他动作自然而轻柔,在她尚未反应过来时,已将那抹翠色,轻轻簪在了她束发的巾冠之侧。
“城中女子踏青,多爱簪花以饰容颜。”他声音温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磁性,“我见你目光流连于那些贵女发间的鲜花,眼中似有欣羡,却每每回避。既不愿簪花,我便折此绿柳赠你。‘戴柳留华年’,阿喜,愿你如这柳枝,常青不败,永葆此刻之真。”
他将手缓缓收回袖中,宽大的袖口掩去了他指尖细微的动作。面具掩去了上半张脸的神情,阴影让他此刻的目光澹澹难辨,那话语似是大有深意,又仿佛只是友人之间随口的祝愿。
令狐喜整个人都僵住了,只觉得心脏在胸腔里毫无章法地剧烈跳动,如同擂鼓一般,震得耳膜嗡嗡作响。
秘密可能被窥破的恐慌,夹杂着一种难以言喻的、被如此细致关注的悸动,瞬间攫住了她。她莫名地紧张起来,声音都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颤:“你……你怎知我……”
“你的事,自然大小我都是上心的。”李悟温声应答,语气自然得仿佛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他对她瞬间异常的神色恍若未闻,心中那份猜测却又笃定了三分。他观人极细微,又善察多疑,对于她的身份,早已存了疑影。只是,以他的性子,绝不会仅凭些许猜测便贸然询问。
想起之前同游曲江丽水畔,宝马香车络绎不绝,许多高门贵女三三两两下辇游玩,她们发间装饰各异,有戴含苞待放的花苞者,有鬓边斜插整朵娇艳桃花者,引得游人频频侧目。他当时曾出言,欲折花为她簪戴,她却寻了借口婉拒。自来长安,男子簪花者亦数不胜数,本是风雅之事,她为何独独对此心慌至此?
若真是李代桃僵之事……他心中暗忖,想起古时花木兰从军的典故。一个女子,要在这满是男子的官衙中,在众目睽睽之下遮掩身份,其间的起居饮食、言行举止、乃至衣袍下的身体变化,无不需要时刻留心,万分谨慎,谈何容易?其中艰辛,恐怕非外人所能想象。
这时,侍立一旁的僮仆恭敬地奉上一直提着的竹篓。李悟接过,从篓中取出一个用新鲜荷叶仔细包裹的物事。他一边动作娴熟地解开系着的细绳,一边自然地转换了话题,仿佛方才那簪柳的举动只是兴之所至,微不足道。
荷叶展开,露出里面码放整齐、造型精巧的点心,仍是令狐喜喜爱的甜食。他将掌中那枚点心递到她的唇边:“尝尝看,临江酒楼新出的冰盏玉莲酥,此时吃,最是解暑。”
甜食烦腻,其实他本人并不喜欢。可既然不喜欢,又为何临时起意,非要绕路,特意多带了些。
令狐喜尚未从方才的心悸中完全平复,见他递食到嘴边,下意识地微微张口,咬了一小口。果然,青团外皮软糯弹牙,内里的豆沙细腻清甜,最妙的是那入口即化的冰凉口感,瞬间驱散了初夏午后的最后一丝烦闷。
她满足地眯了眯眼,像一只被顺了毛的猫儿。随即好奇地回头去看那僮仆放下的竹篓,果然发现篓底铺着大块的坚冰,正丝丝地冒着寒气。她这才恍然明白,为何这一路上,那提着竹篓的小僮仆虽走在荫凉处,却依旧累得大汗淋漓。
就连方才在亭中坐下后,吃的第一个红豆馅青团,入口亦是口感冰凉,软糯弹牙,想来也是同样用冰镇着带来的。
他竟……有心至此。
一股暖流,混杂着冰点带来的清凉甜意,悄然涌上令狐喜的心头。
亭外松涛阵阵,蝉鸣依旧,斜阳将二人的身影在亭中拉得悠长,仿佛交织在了一处。空气中弥漫着艾草的清香、松竹的冷韵。
李悟也拈起一枚青团,却并未立刻食用。他只是看着身旁的她,看着她小口小口、珍惜地品尝着点心时那乖巧又满足的模样,看着她鬓边那片自己亲手为她簪上的翠绿柳叶,在斜阳余晖中微微颤动。
心中因权力争斗而日渐冷硬的荒芜,似乎也在这一刻,被这片小小的绿意,以及眼前这人带来的、陌生而柔软的触动,悄然浸润了一丝生机。
或许,在这步步为营、虚与委蛇的长安,能与一人共享片刻的真心,已是命运予他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