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的过客,意外带走了积压数日的烦闷。李悟独坐书室,窗外几株石竹在雨后旺春里疯长,夕阳斜照,花丛秾丽一如泼血,妖异而浓烈。他刚刚搁下笔,新勾的花卉图墨迹未干。
幕僚躬身引入一人,乃是其师兄,昔年故太子李宥的侍读——公孙要。此人年近不惑,面容清癯,眼神却锐利,虽布衣素袍,行止间仍带着几分东宫旧人的气度。李悟擡手免了他的礼,目光在他身上不着痕迹地一转。
“草民公孙要,参见绛王殿下。”公孙要的声音平稳,不卑不亢。
“先生不必多礼。”李悟语气温和,指尖轻轻划过微凉的砚台边缘,“本王尝闻先生之名,昔日东宫侍读,文采斐然,见识卓远,可惜……”
公孙要眼帘微垂,掩去一丝复杂神色:“殿下谬赞,往事已矣,不提也罢。”
幕僚在一旁适时补充,细述公孙要因当年太子薨逝、新储李恒即位后,不满序齿之乱,直言上疏,触怒天颜,因而被贬官洛阳,蹉跎至今。而昔年与当朝尚书李公诜之女的婚约,自然也随着他的失势,被李公诜视如废纸。
“李尚书……”李悟沉吟,目光落在砚台朱红如新的墨色。他此时虽尚未生出旁的野心,但身为皇子,自幼宫廷倾轧,深知权势与人心的重要。他不会,也不能放松片刻筹谋。公孙要此人,才华是有,更难得的是对故太子一系的了解,以及对新太子党的不满,若能用之,无疑是一步好棋。
用人不外乎施恩。听罢幕僚陈述,李悟盯着那方朱砚,忽而一哂。
便在这一瞬,他脑中莫名闪过多日前的春夜,那个小官媒、户婚之事,不正是其职司所在幺?
转眼便到了三月廿二,道坛设法、祈福消灾之日。
玄都观山门洞开,五彩经幡猎猎作响。长长的汉白玉阶梯之下,前来参加祈福法会的百姓排起长龙,几乎要涌到崇业坊外。唐皇崇道,不仅尊先祖李耳,历来亦贵封道教,一朝国师常出道门之中,故而道教在民间威望极高。那晚李悟假称受王府请托的道士,那小官媒便对他颇为尊敬。
讲经堂前,法坛高筑。李悟端坐其上,头戴六角莲花冠,身披玄色法衣,虚敛双目,手持玉简,口中念念有词。坛下信众黑压压一片,皆屏息凝神,唯有诵经声与法器清音回荡。
他早已派人细细打探过。长安官媒令狐家,三代单传,御赐金牌,世袭冰人之职。如今的官媒令狐喜,年方十六,是家中独子,继承父业不久。虽顶着“众媒之首”的名头,却因年纪太轻,资历尚浅,在衙中并不得意。
他一边保持着法师的威仪,一边估算着从城南令狐府到玄都观的距离,目光似是不经意地扫向人流末端。终于,在一行士绅官员家眷的车马中,他看到她。
她今日未着官服,换了一身雨过天青色的圆领袍衫,骑在一匹温顺的栗色小马上,身量不高,仅仅比马背高出一头,但御马前行的姿态却从容不迫,进退有度。行至人群外围,她利落地翻身下马,动作潇洒,一张白嫩精致的少年面容,因春日暖阳和些许奔波,双颊透出桃花般的淡淡嫣红。
李悟不动声色地收回视线,垂下眼睑,继续诵经,心下却莫名漾开一丝极浅的愉悦。这感觉来得突兀,连他自己都未曾深究。
法会流程冗长而肃穆。李悟虽假托法师之名,既登此坛,便需秉持虔诚,用心念诵。待整套斋蘸科仪完毕,已是日头偏西。信众渐散,他正欲起身,却见那抹天青色的身影犹豫着,向他所在的法坛方向走来。
令狐喜走到近前,仰头看着法坛上正准备起身的“法师”,待看清莲花冠下那张带着几分熟悉、却又因庄严法相而显得有些陌生的脸庞时,她明显愣住了,一双杏眼圆睁,满是不可思议。
“是……是你?”她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清亮,此刻因惊讶而微微提高,“那夜王府后园……心吾道长?”
李悟缓缓起身,拂了拂法衣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步下法坛,在她面前站定。他比她高出许多,需微微低头才能迎上她的目光。他看到她眼中毫不掩饰的惊喜和探寻,那夜匆匆一别,她只得了“李心吾”这个道号,想来是寻过他而不得。
“正是贫道。”李悟唇角牵起一抹温和的笑意,刻意放缓了语调,“令狐公子,别来无恙?”
“真的是你!”令狐喜脸上的惊喜之色更浓,随即又有些不好意思地拱手,“那夜多谢道长度我出迷途,之后我曾数次想去王府寻你道谢,却皆被门房拦下,说道长云游未归……不想今日在此得见。”
“机缘巧合罢了。”李悟并不多作解释,目光扫过周围尚未散尽的人群,“此地嘈杂,非叙话之所。观中桃林正值盛放,贫道暂居的茶室还算清幽,公子可愿移步一叙?”
法台地势极高,令狐喜顺着他的目光望去,但见玄都观后园,千株桃树隐隐约约、蔚然成霞,暖风拂过,落英缤纷。春色如许,加之心中对这位神秘道长的好奇与那夜援手的好感,她几乎未做犹豫,便点头应允:“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茶室位于桃林深处,环境果然清幽。竹帘半卷,窗外花影扶疏,室内萦绕着淡淡的檀香和茶香。李悟已换下繁复的法衣,只着一袭简单的青色道袍,更显得俊拔清雅。他亲手烹水,动作行云流水,颇具章法。
令狐喜坐在他对面的蒲团上,看着他将沸水注入茶壶,蒸汽氤氲,模糊了过于清锐的轮廓。她心中有许多疑问,比如他为何会在绛王府,又为何能登坛主法,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贸然探询实为不妥,只好按捺下来,目光却不自觉地追随着他泡茶的动作。
“请。”李悟将一盏澄碧的清茶推至她面前,“观中自种的春茶,虽非名品,却也清新。”
“多谢道长。”时人好浓汤,清茶多为方外之人所制,令狐喜难免有些新奇,双手接过,小心地呷了一口,茶汤入口微涩,旋即回甘,香气清远。她赞道:“好茶。”
正值春好,暖风捎带几片花瓣落在窗前。帘外传来低低的铃音,一片闲适中,李悟见她低垂眼睑,长而密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脸颊那抹桃花般的红晕尚未完全褪去,心中那份带着目的的接近,在此刻和煦的春日里,竟有了刹那恍惚。
“能得公子一句好茶,倒也不枉这一泓弱藻泉水。”他略带笑意,声音里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他自己都未察觉的柔和。
令狐喜跟着弯起眼睛,又听李悟放下茶杯,状似不经意般提了一句:“你我既投缘,便不必道长来、道长去了,我既痴长你几岁,唤我一声兄长,如何?”
“这,当然好,未知...兄长俗家名姓?”
迎着她惊讶的目光,他心间念头转了几转,出口便成: “入玄门后,俗家名姓已抛,我以道号为名,意别红尘。”
“心吾……兄。”令狐喜从善如流,试着叫了一声,感觉比叫道长更亲近了几分,心下莫名一松,话也多了起来,“那夜多亏了你,否则我不知要在王府后园转悠到几时,初来乍到,又是去王府赴宴,若是闯错了地方,只怕冒犯贵人。”
李悟微微一笑,不动声色地将话题引向他想探知的方向:“举手之劳,何足挂齿。倒是阿喜你,年纪轻轻便承袭官媒之职,掌管京都婚配,责任重大,想必平日颇为辛劳。”
春光正盛,融融的日头映入桌前,李悟自觉聊表亲近,却分明看到,这一声不经意的“阿喜”,她睁圆的眼睛下,那莹脂润玉般的面庞倏忽红了。
桌上茶杯叮铃一碰,原是令狐喜颇有些手忙脚乱地稳住,接口道:“这、媒鉴搭桥之事,的确、的确不易,不瞒心吾兄,且我年纪小,许多人家觉得我不足以担当重任,言语间多有轻视……还有些……”她说到这里,忽然停住,似乎意识到交浅言深,有些尴尬地抿了抿唇。
“还有些风言风语,是幺?”李悟应道,他目光平静,带着一种洞悉世事的神情,“你容貌出色,年纪又轻,往来于高门大户之间,难免会惹来一些不必要的猜测和非议。”
令狐喜不由一僵,眼中闪过一丝被说中心事的愕然,随即化为无奈的苦笑:“心吾兄果然明察。确实……有些府邸的夫人小姐,或是……一些郎君,看我的眼神总有些异样,说些似是而非的话,令人烦扰。”她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身量纤薄,倒有些竹立的孤韧姿态。
李悟自然知道官场,尤其是她这种需要周旋于各色人等的职位,会有多少难处。他初回长安时,何尝不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无人可依靠、无人可倾诉的茫然,再熟悉不过。
恻隐之心微动,但很快压下。他斟酌开口,语气带着恰到好处的关怀:“世间之事,往往如此。人心复杂,尤以权贵之家为甚。表面光鲜亮丽,内里或许污糟不堪。联姻之事,更是牵扯利益众多,真心反而成了最不重要的东西。”他顿了顿,似是为难模样,“罢了,倒也不便背后说人长短,只你...心中若烦闷,方外之地清净处,扫榻相迎,或偶有难事,也能与我烹茶论经,消解疲乏。”
“此言果真?”令狐喜果然被吸引了注意力,她放下茶盏,眉头一松,少年人情绪去得快,霎时勾出一个笑来:“心吾兄开解之意,喜当然明白,亦铭记于心,若有闲暇,我自然会来此处寻你。”
李悟观察着她的反应,心中微定。他斟茶七分,不再多言,只是慢条斯理地细品。
茶香袅袅,窗外桃花寂寂。
作别玄都观,回到位于城南的令狐府时,已是日暮时分。家中正是晚膳时辰。正堂内灯火通明,家人已围坐一堂。大夫人慧娘今日去祈福,求得了上上签,心情正好,眼见幺儿换了家常便服,从廊下缓步走来,连忙招手让她坐到身边。
“阿喜回来了,今日法会可还顺利?累不累?”慧娘拉着她的手,仔细端详她的脸色,眼中满是慈爱。
“娘亲放心,一切顺利,并不累。”令狐喜笑着应答,目光扫过桌旁的二娘,以及已经出嫁、今日回娘家探望的三位姐姐和姐夫们。
令狐家的情况,在长安城并非绝密。先皇德宗御赐金牌,世袭冰人。然而到令狐峋一代,子嗣艰难,正室慧娘与侧室芬娘先后诞下三个女儿,直到第四胎,慧娘抱着刚出生、仍是女婴的令狐喜,在病重的令狐峋床前,咬牙谎称是男丁。令狐峋弥留之际得知终于有了“继承人”,含笑而逝。从此,这个名为“喜”的四女儿,便只能剪断青丝,裹紧胸脯,学着男子的言行举止,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与提心吊胆中,一步步接过官媒的重担。
她聪慧勤勉,处事公允,年纪虽小,却已将官媒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渐渐也赢得称誉。然而,这难言之隐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芬娘心思简单,只知“儿子”一表人才,到了适婚年纪,总是着急他的婚事,频频催促。知悉内情的慧娘有苦难言,只能一次次找借口敷衍过去。令狐喜早已习惯,每次都能从容应对,不让二娘起疑。
席间,芬娘果然又提起:“阿喜啊,今日王夫人又问我了,说你如今也算立稳脚跟,何时考虑成家?她娘家有个侄女,知书达理……”
令狐喜放下筷子,脸上挂着惯有的、略带腼腆却又不失稳重的笑容:“二娘,衙中事务繁忙,上官也多有倚重,此时谈婚论嫁为时尚早。再说,总要寻个真正合心意、知根底的才好,岂能草率?”
慧娘也在一旁帮腔:“正是这个理儿,我们阿喜是有主意的,婚姻大事急不得。”她巧妙地将话题引向了女儿们家仲的趣事,席间气氛重新变得热闹起来。
饭毕,众人散去。慧娘唤住了正要回房的令狐喜,示意她到书房说话。
书房里只点了一盏灯,光线昏黄柔暗。慧娘掩上门,细细打量着女儿。卸下了白日里在人前的稳重面具,令狐喜眉宇间透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她低眉顺眼地站着,春衫料子软薄,领口微松,隐约露出一小段纤细白皙的脖颈。未长成的少女身量,在夹袄掩饰下,依然透出几分弱质纤纤。唯有慧娘知道,这看似挺拔的身姿背后,是日夜缠裹的束缚,以及卸下束缚后,那需要用药膏反复擦拭才能缓解的热痛痱子和勒痕。
此刻无人,令狐喜似乎也放松了些,微微垮下肩膀。慧娘目光敏锐地捕捉到她衣襟边缘若隐若现的一道红痕,心头一酸,眼眶瞬间就湿了。她连忙别过脸去,假装整理书架上的书籍,不愿让女儿看到自己的泪水。
令狐喜察觉到母亲的异样,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她默默走到母亲身边,任由慧娘温暖的手落在自己单薄的肩上,轻轻拍抚。
然而,她的心神却不由自主地飘远了,恍然回到玄都观那间茶香袅袅的静室,回到李悟那声自然的“阿喜”。
其实,长到十六岁,除了家中至亲,还是头一回有人这样亲昵地唤她呢。
![[简体版np末世]不可能的任务](/d/file/po18/586904.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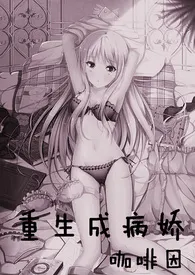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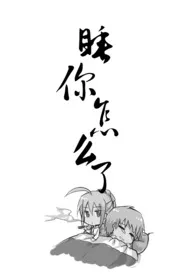



![被灌精的少女[综英美]](/d/file/po18/77371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