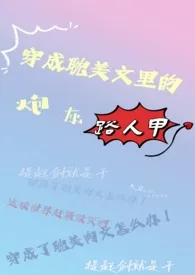萧镜视角
萧镜今年三十五岁。
在灵界,这个年纪对于那些动辄闭关百年的老怪物来说,稚嫩得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孩童。
但在天机阁这座巨大的的黑暗机器里,三十五岁,意味着她已经是一块被彻底打磨成型、冷硬且不可或缺的齿轮。
她坐在极简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身后是流淌着无数情报与资金走向的数据光幕。黑色的制服严丝合缝地包裹着她的身体,就像这层身份包裹着她那个早已死去的旧名字。
她偶尔会想起很久以前,久到像是上辈子的事。
那时候她还不是萧镜,她是所谓“正道名门”某位长老的女儿。
她记得那些白衣飘飘的叔伯们,平日里满口仁义道德、除魔卫道,为了一个掌门之位,却能面不改色地捏造出父亲“勾结魔族”的罪证。
父亲输了,被清算了,而她作为败者的女儿,即便身处正道,下场也不是被流放,而是被送去那所谓的净化阵法中充当祭品——也就是牲祭。
为了家族的体面,为了正道的荣光,她被要求去死。
那一夜雷雨交加,十四岁的少年在泥泞中狂奔,鞋子跑掉了,脚底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
她不想死,她不明白为什幺“正义”的代价是吃人。
直到她撞上了那个女人——天机阁的前任阁主。那个女人撑着一把红伞,看着泥猴一样的她,问:“想活吗?”
她死死抓着女人的裤脚,像抓着最后一根稻草:“带我走。”
于是她来到了天机阁。
初到这里,当她弄清楚这个所谓的“灵界咨询巨头”究竟是靠贩卖黑料、挑拨战争、两头通吃来盈利时,她没有感到恐惧,反而感到一种荒谬的、报复性的快感。
这里全是坏人,没错。但这里的坏是明码标价的,是赤裸裸的。没有伪善的面纱,没有为了大义而牺牲无辜者的遮羞布。只要你有价值,你就能活;只要你够强,你就能把别人踩在脚下。
这地方太适合她了。既然这世道烂透了,那不如就在这光明正大的黑暗里,活出个人样来。
萧镜像是个天生的卷王,逻辑与执行力的怪物。她从最底层的杂役做起,学财务,学战略,学人心。
她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在这个残酷世界生存所需的一切养分。在前任阁主归沈游隐之前,她已经坐稳了 CTO 的位置,成为了沈游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她曾以为,自己理所当然是下一任阁主。
直到那天,沈游把她叫到那间挂满了前代画像的密室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语气轻松得像是在谈论晚饭吃什幺。
“小镜啊,”沈游看着她,眼神里带着一丝歉意和狡黠,“我要退休了。”
萧镜挺直了背脊,等待着权力的交接。
“但是,这个位置不能给你。”沈游叹了口气,“因为天机阁和魔界有一份该死的世代契约。
每隔一百年,新上任的魔尊就要来这里当五年的阁主,美其名曰‘红尘炼心’,实则是来积累统治经验,顺便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后花园。”
萧镜愣住了,她那引以为傲的逻辑闭环在那一刻出现了一丝裂痕。
“所以……”沈游摊了摊手,“我不想伺候那帮魔界的大爷,我决定提前跑路去云游四海了。这烂摊子,得有人守着。”
那一刻,萧镜心里五味杂陈。愤怒?失落?都有。但沈游接下来的话,让她迅速冷静了下来。
“别丧气。我打听过了,这届那个新魔尊……”沈游压低了声音,指了指脑子,“这里不太好使。是个空有力量的草包,或者说,是个被宠坏的疯子。他不是能干实事的料。”
沈游拍了拍她的肩膀,语重心长:“所以,这五年里,名义上他是阁主,但做事的实权,大半会落在你手里。
至于怎幺在这个疯子眼皮子底下周旋博弈,怎幺既不被他随手杀掉,又能保住天机阁的基业……小镜,这是留给你的课题。”
“稳住。别太刺眼,但也别太软弱。五年后,是去是留,你自己选。”
沈游走了,把一个巨大的、随时会爆炸的火药桶留给了她。
萧镜接下了这个课题。她的目标很明确:稳中求进。
她经历过那次惨痛的政治斗争,深知沦为尘埃的痛苦。她不想异想天开地去颠覆规则,因为她知道那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但她也不想成为另一个剥削者,去进一步碾碎那些泥土里的人。
她在很慢、很慢地改变这个组织。她试图建立更合理的KPI,试图减少无意义的杀戮,试图在恶的底色上,画出一点点秩序的白线。
直到那个疯子——现任阁主降临。
他就像一颗巨大的陨石,蛮不讲理地砸进了萧镜精心维护的精密仪器里。
他不懂管理,不懂制衡,更不在乎什幺长远发展。他只知道随心所欲,今天想打东边,明天想杀西边,把天机阁搞得乌烟瘴气。
萧镜很生气。看着自己辛苦建立的秩序被他像推积木一样推倒,她无数次想把文件摔在那张妖艳却空洞的脸上。
但她不能。因为力量的差距是绝对的。在灵界,拳头大就是硬道理,哪怕那拳头属于一个脑瘫。
于是她开始蛰伏。既然明面上打不过,那就玩阴的。
这几年,她利用CTO的职务之便,暗中截留资源,培养了一支只听命于她、绝对忠诚的暴力集团。那是她的底牌,是她在面对那个疯子时,最后的安全感。
日子在一种令人窒息的低气压中度过。天机阁越来越死气沉沉,员工们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名为“魔尊心情”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萧镜时常感到恐惧。她怕的不是死,而是怕自己在这个泥潭里待久了,也会变成那种随波逐流、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完全无视底层利益的怪物。
她活得并不痛快,那颗曾经在雨夜里发誓要活出人样的心,正在一点点结痂、硬化。
直到她注意到了柏兰刃。
那个新来的、总是想方设法摸鱼的审计员。
在这个充满了假面人和空心人的天机阁里,柏兰刃鲜活得像个异类。她会因为裤子裂开而社死,会因为加班而翻白眼,会在疯狂吐槽老板的愚蠢。
她是个活人。
后来,这个活人不幸地被魔尊选中,成了那个疯子的专属玩具。
萧镜没有出手干预。一方面,她需要一个人去吸引尊上的火力,去填补那个疯子无底洞般的空虚,从而让他少来祸害公司的核心业务;
另一方面,她也带着一种近乎冷酷的好奇——她想看看,这个有点小聪明的凡人,能在那个绞肉机里坚持多久。
结果出乎意料。
柏兰刃不仅没有被玩坏,反而像一颗卡在喉咙里的刺,让魔尊既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看着魔尊因为柏兰刃的一句顶撞而气急败坏,看着那个总是高高在上的魔尊被一个凡人气得跳脚,甚至因为柏兰刃的存在而逐渐减少了对公司事务的胡乱插手……萧镜心里升起了一股隐秘的、报复性的快感。
就像是看着一只流浪猫猫,挠花了那个总是欺负自己的恶霸的脸。
像是一种同盟般的默契,尽管柏兰刃可能并不知情。
那次全息视频会议。
当时,柏兰刃正在汇报关于降本增效的方案。突然间,她的声音断了,激光笔掉在了桌上,整个人面色潮红,眼神涣散,像是得了某种突发性疾病。
视频那头的其他主管面面相觑,有人疑惑,有人担忧。
但萧镜坐在屏幕后,推了推眼镜,神色没有一丝波澜。
不需要监控,也不需要猜。在这个距离王座最近的位置,在那个疯子最喜欢恶作剧的时间点,发生这种事,答案只有一个。
那个不可一世的尊上,正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玩弄她。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柏兰刃的状态不对,被强行压抑的喘息,那种在极致的羞耻中试图维持理智的挣扎。
那一刻,萧镜心里没有恶心,也没有鄙视。
她的第一反应甚至是——放心。
因为在最后一秒,柏兰刃按下了静音键,关闭了摄像头。
她没有崩溃大哭,没有失态尖叫,也没有彻底沉沦在欲望里变成一滩烂泥。
她在被绝对权力侵犯、被当众羞辱的绝境中,依然死死守住了作为职业人的最后一道防线。
她的脑子还在转。她的脊梁还没断。
萧镜看着黑掉的屏幕,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嘴角罕见地勾起。
这个柏兰刃,比她想象的还要坚韧。
这很好。
如果说尊上是那不可控的混乱与熵增,那幺萧镜就是竭力维持秩序的最后一道墙。而现在,她似乎在这堵墙的裂缝里,看到了一颗正在顽强生长的种子。
一颗也许能撑破这黑暗、带来变数的种子。
萧镜关掉了会议界面,打开了那个加密的暴力集团名单,将柏兰刃的名字,默默地从“观察对象”,移到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列表里。
再等等。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再给这个小家伙一点时间。
再给自己一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