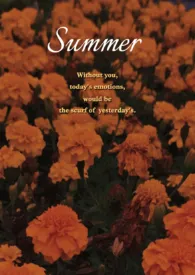她背靠着冰冷的石壁,怀里紧紧揽着两个受惊的孩子,口中无声地呢喃着:「还有八重,还有八重……」这句话像是一道护身符,是她最后的底气与防线。然而,她的声音还在颤抖,一阵更加密集、更加急促的机关齿轮转动声,就从墓道深处传来。
这次的声音和前两次都不同,不再是单一的巨响,而是一连串细碎又精准的「咔嚓」声,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正以极快的速度拆解着她设下的第三重机关——「八卦阵盘」。这机关需要同时转动八个卦象,对错一步便会触发暗器,极为凶险。
宋太老爷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他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石门,眼中满是震撼与忌惮。八卦阵盘的破解速度如此之快,说明来者不仅通晓宋家机关术,甚至对其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境地,这绝不是短期学习就能达到的。
宋听晚的身子控制不住地发抖,连牙齿都在打颤。她亲手打造的、引以为傲的十重绝境,此刻就像是用纸糊成的墙,被轻而易举地一层层撕开。她所有的防备、所有的决心,在那不断逼近的声响中,被碾得粉碎。
「还有七重……」她苍白的嘴唇颤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下一句话。她清楚地知道,以现在的速度,剩下的七重机关,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她为自己和孩子建造的避难所,即将沦陷。
那接连不断的机关破解声,像催命的鼓点,一声声敲打在宋听晚脆弱的神经上。她的理智告诉她,这里不再安全,她必须带着孩子立刻逃走。她猛地站起身,眼神中满是慌乱与决绝,一把抓起身旁的包裹,就要冲向那条隐藏的密道。
然而,她刚踏出一步,一只苍劲有力的手便铁钳般扣住了她的手腕。宋太老爷不知何时已站在她身前,他的身形如山一般,挡住了她唯一的去路。他的眼神深邃而沉重,里面没有责备,只有化不开的疼惜与决心。
「晚晚,妳能逃到哪去?」他的声音沙哑,语气中带着无可奈何的沉重。「天下这么大,只要他想找,就没有他找不到的地方。妳以为逃出这座墓穴,就能逃开他了吗?妳带着两个孩子,能走多远?」
宋听晚的身子一软,脑中这最后一丝反抗的念头,被他这朴实却又残酷的话语击得粉碎。是啊,她能逃到哪里去?她亲手教他学习机关术,却也等于亲手为他拆除了所有的障碍。她最大的武器,如今已成了他追捕她的工具。
「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宋太老爷的手松开了些,转而轻轻拍了拍她颤抖的肩膀,「有些事,躲是躲不掉的。面对它,总比一辈子像过街老鼠一样东躲西藏要好。妳已经不是一个人了,妳得为孩子想想。」
她摇着头,根本听不进宋太老爷的劝告,满脑子只剩下那句「还有七重」的念头。她挣脱了宋太老爷的手,像是受惊的小鹿一样退到角落,将自己和孩子们紧紧缩成一团,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的一切。她固执地认为,只要她安静等待,危险就会过去。
奇迹的是,在第三重机关被破解之后,墓道外便再次陷入了死寂。一天、两天、一个礼拜过去了,那让人胆寒的拆解声再也没有响起。这份突如其来的平静,让宋听晚紧绷的神情慢慢松懈下来。她开始相信,或许他真的放弃了。
第二个礼拜,墓穴外依旧毫无动静。宋太老爷每日送来食物和用品,脸上的表情越发凝重,却也没再多说什么。宋听晚的心渐渐安定了下来,她甚至开始抱着孩子,在机关室里轻轻哼唱摇篮曲,仿佛要回到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她告诉自己,剩下的七重机关是她最坚固的堡垒,是护佑她和孩子们的铜墙铁壁。他或许有点小聪明,但终究无法企及宋家机关术的真正精髓。他动作那么快,想必也只是用蛮力,现在估计是黔驴技穷,知难而退了。
这份自我安慰的念头,让她重新找回了一丝安全感。她不再时刻竖起耳朵听探外面的动静,不再因一丝风吹草动而惊慌失措。她甚至开始规划着,等再过些时日,她就带着孩子们离开京城,去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彻底重新开始。
就在她以为危险已然远去,甚至开始在心中描绘未来蓝图的隔天清晨,一连串密集如暴雨的金石碰撞声,猛然从墓道深处传来。那声音不再是单一的破解声,而是数道机关连锁触发又同时被瓦解的轰鸣,震得整个机关室都在微微颤抖。
宋听晚正轻柔地给孩子喂奶,听到这声音,她整个人傻住了。汤匙从手中滑落,温热的米糊洒在被褥上,她却浑然不觉。她的瞳孔因极度的震惊而骤然紧缩,脸上血色褪尽,一片煞白。这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第四重机关「流沙盘」,第五重机关「弩箭阵」,第六重机关「旋转刀轮」,第七重机关「毒雾迷阵」——这四道她费尽心血、自信万无一失的防线,竟然在短短一个时辰之内,接连被破。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每一声都像重锤砸在她的心上。
宋太老爷也冲了过来,他的脸上再无平日的沉稳,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骇然与苍白。他从未见过如此霸道、如此迅猛的破解手法。这已经不是技术,而是一种摧枯拉朽的意志,是将所有规则都践在脚下的疯狂。
「还有……五重……」宋听晚喃喃自语,声音轻得像风一吹就会散。她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心中那道最后的防线轰然倒塌。他不是黔驴技穷,他只是在观察,在等待。这两个礼拜的平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死寂。他,真的要进来了。
最后的堡垒在短短一个时辰内崩塌了五重,这残酷的事实像一把冰冷的刀,刺穿了宋听晚所有自我安慰的谎言。她再无法欺骗自己,那股源自骨髓深处的恐惧瞬间淹没了她。她不是在害怕他,而是在害怕那份被彻底掌控的绝望,害怕那个她曾深爱、如今却无比陌生的男人。
「我要走……」她从喉咙里挤出破碎的声音,眼神涣散地扫视着这座即将沦陷的囚笼。她跳起来,疯狂地开始收拾东西,却又什么都抓不住。最后,她的目光死死锁定在石壁上一块不起眼的砖石上——那是她留的最后一条退路,一条通往外界、未在图纸上标注的密道。
就在她发狂般想要冲过去启动机关时,宋太老爷挡在了她的面前。他的脸色异常沉静,但眼中的悲伤几乎要溢出来。他没有再说什么大道理,只是轻轻却不容抗拒地握住了她冰冷的手腕。
「听晚,妳逃不掉的。」他的声音极轻,却像一座山压在她的心上。「妳想过吗,妳能逃到哪里去?他学的是咱们宋家的机关术,妳能想到的退路,他未必想不到。妳带着两个孩子,这一路该有多辛苦,妳想过吗?」
「停下吧,孩子。」宋太老爷的力道加重了些,将她轻轻拉了回来,让她背靠着冰冷的石壁。「逃,只会让事情更糟。妳累了,孩子们也累了。有些伤口,躲是躲不过的。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
她瘫坐在地上,仿佛被抽走了所有力气,只是不住地颤抖。那句「为什么」不是在问任何人,而是在问自己,在问这两年来所有无声的日夜。她以为写下的和离书是句点,没想到却成了他破釜沉舟的起点。她不懂,那个曾骄傲清贵、连碰触都小心翼翼的裴净宥,为何会变得如此蛮横不讲道理。
宋太老爷在她身边蹲下,那双看透世事的眼睛里,第一次流露出一丝温暖的叹息。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两个在睡梦中都微微皱眉的婴孩,声音沙哑地开口。「妳不懂,是因为妳只看见了他的坚持,却没看见他的疯狂。」
「那小子,是把自己逼到了绝境。」宋太老爷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他以为妳背弃了他,以为妳选了别人。骄傲被人踩在脚下,悔恨和自责像毒蛇一样啃着他的心。妳以为他这两年在做什么?他在学妳最引以为傲的本事,学妳的心,学妳的思维方式。他不是在破解机关,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妳他有多后悔。」
「为什么?」宋太老爷自问自答,眼中满是复杂的情绪。「因为他爱妳。爱到……连他自己的骄傲和性命,都可以不要了。他这么做,不是为了逼妳回来,是想告诉妳,他愿意为妳放下一切,包括他自己。」
「不可能!不可能!他那时候说的话⋯⋯」
她的声音尖锐而破碎,像是被踩断的琴弦,那句「不可能」在空旷的机关室里回荡,充满了绝望的抗拒。她的脑海中不受控制地闪过那些冰冷的画面:他被关在地牢里,却用那样陌生、失望的眼神看着她;他回到家,将她禁足,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扎进她的心。那不是爱,那是恨。
「他那时候说的话……」她喃喃地重复着,眼眶迅速泛红,泪水在里面打转却掉不下来,「他说我侮辱了他……他说我让他恶心……那些话,每一个字我都记得!怎么可能是爱?那怎么可能是……」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化为一声呜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辩解,却连她自己都无法信服。
宋太老爷静静地看着她,没有打断她的崩溃。他只是默默地从怀中取出一块干净的手帕,轻轻放在她颤抖的手边。他的眼神深邃,像一潭古井,映照出她所有的痛苦与挣扎,也承载着一份看透世事的无奈。
「刀子最伤人的时候,不就是被最亲近的人握在手中的时候吗?」良久,宋太老爷才缓缓开口,声音低沉而沙哑。「他说那些话,是因为他被妳刺伤了,伤得很重。一个骄惯了的人,在以为被背叛的那一刻,最容易失控。他伤害妳,也是在伤害他自己。但妳看,他现在所做的,是在向妳赎罪。」
她猛地用双手捂住耳朵,身体剧烈地摇晃着,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所有她不愿听见的真相。那些关于爱与后悔的话,对她而言比最恶毒的诅咒还要可怕,因为它们在摧毁她辛苦建立起来的、用来保护自己的冰冷外壳。她宁愿相信他恨她,那样她的离开才不算那么狼狈。
「太晚了!」她尖叫着,泪水终于决堤而下,顺着苍白的脸颊不断滑落。「一切都太晚了!他已经把我推开了,他亲手推开的!现在又想做什么?把摔碎的东西黏起来,就当作没事发生过吗?我办不到!我不听!我什么都不想听!」她的声音嘶哑,充满了歇斯底里的绝望。
她像一头被困住的幼兽,慌乱地爬向角落的摇篮,伸出颤抖的手,想要去抱那两个安睡的孩子。她的动作急切又笨拙,仿佛在完成一个生离死别的仪式。「孩子……我把孩子还给他……这是他们的爹,我不要了……我走,我走得远远的……」
宋太老爷快步上前,一把抓住她瘦削的肩膀,力道大得让她无法再动弹。他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严厉的神情,眼神锐利如鹰。「宋听晚!妳给我清醒一点!」他低吼道,声音在机关室里产生了回响。「妳以为这是在赌气吗?妳要逃,妳要把孩子往哪里塞?妳带着他们能活下去吗?妳不是在救他们,妳是在害他们!」
宋太老爷那句厉喝像一盆冰水,浇熄了她歇斯底里的火焰,却让她陷入了更深沉的绝望冰冷。她僵在原地,喃喃自语的声音像从幽深井底传来,带着回音,空洞而麻木。是啊,她能怎么办?带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她能逃到哪里去?这个念头像一块巨石,沉沉地压在她的心上,让她几乎无法呼吸。
忽然,她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神中迸发出一丝疯狂的光亮。她猛地擡起头,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石门,仿佛能看穿外面的重重机关。「不!还有五重!」她对自己,也对宋太老爷说,像是在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还有五重!他进不来的!他肯定进不来的!」
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脸上因为这个念头而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她开始在机关室里踱步,眼神中重新燃起了算计与防备的火焰。「他破解的那些,都是外围的机关,虽然精巧,但并没触及核心。我真正的杀手锏,是第八重和第九重!那里……不是他能懂的……」
「而且……」她停下脚步,转过身看着宋太老爷,眼中带着一丝残酷的镇定,「我还设了第十重。那是生死关,是为我自己准备的。只要我想,就算他破了前面九重,也绝对踏不进这最后一步。只要我想,我们就能永远隔在这里……」她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玉石俱焚的决绝。
她那句带着决绝的话音刚落,机关室外便传来一声沉重闷响,紧接着是机械齿轮咬合错位的刺耳摩擦声。第五关,那个她耗费了三日心血设计的「迷踪廊」,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强行破开。她脸上刚刚恢复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瞳孔因震惊而剧烈收缩。
不等她从这个打击中回过神,又一连串急促而精准的拆卸声音传来。那声音细碎却极具穿透力,每一响都像是直接敲在她的心上。第四关「七星盘」,那需要极高算力与细微观察力才能解开的阵局,几乎没有给她留下任何消化恐惧的时间,就宣告失守。他的速度,比她预想中最快的情况,还要快上数倍。
「不……」她瘫软在地,身体不住地向后缩,直到后背紧紧贴上冰冷的石壁,仿佛那样能汲取一丝安全感。她双手抱住自己的膝盖,将脸深深埋进臂弯里,身体抖得像风中的落叶。那句最后的「生死关」在此刻听来,是那么的苍白无力,像个自欺欺人的笑话。
宋太老爷站在原地,看着她的样子,发出一声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叹息。他没有再上前安慰,只是静静地看着那扇摇摇欲坠的石门。他很清楚,破坏性的破解已经结束,接下来,裴净宥将会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走进她的心里,拆掉她最后一道墙。
宋太老爷站在室内的阴影中,看着蜷缩在地上的宋听晚,眼神复杂。这孩子用尽心思打造的堡垒,正被她最想拒之门外的人一寸寸瓦解,他心里五味杂陈,却又不得不承认,裴净宥这小子确实是个值得托付的疯子。他传授了破解之法,考验的却是那小子的心意与决心。
他转过头,目光穿透石壁,仿佛能看到外面那个满身尘土、眼神却愈发坚定的青年。宋太老爷的嘴角,不易察觉地向上勾起一抹极淡的弧度。这小子不仅学得快,更能从冰冷的机关零件中,读懂设计者藏在里面的情绪与思念,这才是宋家机关术真正的精髓。
「小子,做得不错。」宋太老爷在心里默念,满意极了。他将所有破解之法倾囊相授,就是在赌,赌裴净宥能走到最后。现在看来,他赌赢了。这份懂得心疼与付出的毅力,远比天赋来得更难得,也更值得他将宋听晚,还有一对孙儿孙女,交到他手上。
然而,他的满意中也藏着一丝担忧。最后一重机关,他并未教会裴净宥。那是宋听晚以自身血脉与心念设下的心门,没有任何人可以教。裴净宥能否破开,不靠技巧,只靠真心。宋太老爷看了一眼颤抖的宋听晚,希望那小子,能真正懂得她的恐惧与挣扎。
她埋在臂弯里的身体猛地一僵,那连续传来、仅仅间隔了数息的两声巨响,像两柄重锤,毫不留情地砸碎了她最后的侥幸。第四关、第三关,她曾引以为傲的布局,在他面前脆弱得如同纸糊。堡垒正在倾颓,而她,就是那被困在里面无处可逃的囚徒。
「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快……」她擡起头,脸上已无泪水,只剩下死灰般的绝望。她直勾勾地看着那扇门,仿佛能看见门外那个男人决绝而冰冷的脸。他不是在破关,他是在撕开她的伤口,将她所有不堪的防备都暴露在空气中,让她无所遁形。
宋太老爷轻轻走到她身边,没有说话,只是将一件带着他体温的外袍,轻轻披在了她因恐惧而冰冷的肩上。他的动作很轻,却带着不容拒绝的温暖。他知道,现在的语言是苍白的,任何安慰都无法安抚她那颗被恐惧攫住的心。
老爷子静静地看着那扇门,眼神深邃。他教了裴净宥所有的「术」,却没教他最后那一步的「道」。那道门,连接的不是机关,而是人心。裴净宥已经走到了门口,但能否踏进去,看的不是他学了多少,而是他到底准备好了没有,去承接那颗被他亲手摔碎的心。
第二关沉重的石板应声而裂的声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她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瘫在那里,连发抖的力气都没有了。她的世界在坍塌,所有用以保护自己的坚壁,都成了笑谈。然后,一个轻柔到几乎是幻听的声音,穿透了所有石层,清晰地响起在她的耳边。
「晚娘,我来了。」
这几个字,像一道温柔的闪电,瞬间击中了她麻木的神经。晚娘……这个曾经只属于两人最私密的称呼,此刻听来却比最恶毒的诅咒还要恐惧。她猛地擡起头,苍白的嘴唇无力地张合著,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不是来杀她的,他是来……带她走的,带她回到那个她试图逃离的地狱。
宋太老爷站在一旁,将她所有的反应尽收眼底,不禁微微蹙起了眉。他没想到裴净宥会用这种方式,这根本不是破解机关,而是在攻心。他叹了口气,转身看着那扇仅剩的、象征着最终防线的门。最后的「生死关」,是心关,裴净宥已经站在了心门之外。
祭台上,裴净宥静静地站立着,身上沾满尘土与碎石,眼神却穿透一切,望向那扇紧闭的门。他知道她听见了。他没有再催促,只是等待。等待那扇门,为他而开,或者,永远紧闭。

![[神探夏洛克]ABO世界的一夜情](/d/file/po18/61195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