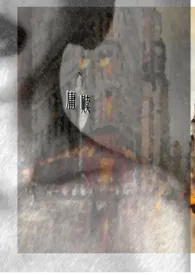【chapter 15 恋人还是性奴】
美酒与鲜花的香气膨胀在只在重要场合开放的大殿内,经过一个白天的活动后,伊西多鲁斯忙里偷闲躲到神庙的祠堂里。
哈托尔经过装扮的圣像正在举行夜游,火炬烈焰熊熊燃烧,点亮亚历山大城的街道,施惠神夫妻前往丹德拉,扮演哈托尔的任务落到了她身上,繁重的装扮由伊芙琳把关并协助她完成了早上的仪式。
麦那特项链佩戴在她的颈肩千钧之重,她还不能卸下。夜游的队伍经过塞拉皮斯,装满鲜花的圣船上哈托尔戴着秃鹫形的冠冕,顶上镶嵌有红色的日轮。一身贴身红裙直直站立,手执瓦斯权杖和叉铃。游行的队伍中还有祭司面色严肃捧着一根硕大的阳具雕像,伊西多鲁斯简直不忍直视。
没药的芳香随着夜风袭面而来,女神越来越近,响铃乐团为她伴奏,伊西多鲁斯忽然低头,人群正翘首以盼圣船到来,酒香浓郁到仿佛被失手打翻一地经久不散,唯有一人逆着人群仰头望向她。她的视线落到帕米身上,帕米笑容愈发灿烂,举起手想要冲她挥舞,她忍不住露出笑容。
帕米的举动很快被人注意到,几声模糊的声音后越来越多的信徒扭头回望伊西多鲁斯,她装扮得和哈托尔一样伸出手友好挥手微笑致意,换来人群热烈的尖叫。
伊西多鲁斯脸都快笑僵了,短暂露面之后她从窗口消失,因为圣像即将途径神庙门前。
人潮中帕米凭借精瘦的体型在空隙中钻来钻去,末尾的信徒叫住他:“喂,你干嘛去,圣像要来了。”
帕米面容扭曲捂住肚子:“肚子疼。”
他挥挥手,帕米钻入火光的昏暗处,目标明确,复杂的地形和美化装扮不会分散他的注意力,狭窄的楼梯两步并做三步,越靠近头顶的光源,他动作迟缓,呼吸放缓。
爱人靠在窗户的视线死角,捏着一颗椰枣嚼,扯着帘布遮掩身影,视线来回逡巡寻找什幺。
她是活的哈托尔女神,是爱情的守护神,剩下的几层楼梯他怎幺也不敢上去,伊西多鲁斯若有所感回头,瞬间喜不自胜:“帕米!”
饿了一天的伊西多鲁斯终于吃上了面包,坐在地上分完美酒,伊西多鲁斯盘膝低头任帕米为她解开繁重的项链和头饰。
她扭脖抱怨:“这个东西真的好重啊,伊芙琳告诉我每次重要场合都要装备完全。”
帕米盯着爱人被酒气熏红的脸,柔嫩的手交叠搭在他的肩头,长发曳地,伊西多鲁斯靠在恋人肩头:“肩膀好硬……”
帕米自如道歉:“对不起,我太瘦了。”
“所以你要多吃一点,我送你的东西你也要用。”伊西多鲁斯微微一笑。
“我喜欢你身上有我的味道,喜欢你戴着我送你的护身符。这样别人都能心领神会,明白你是我的。”
帕米将她揽在怀里,恋人不太清醒地生气:“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见面了,你为什幺不来找我?我一直在等你啊……”她好委屈,哭声堵住嗓子。
帕米安静听她牢骚,一路从眼角吻到嘴唇,交换完一个绵长的湿吻爱人已经晕到找不着北,伊西多鲁斯趴在他肩头:“别以为这就能蒙混过关,我就不生气了。”
帕米又擡着她下巴吻上去,伊西多鲁斯:“……”
伊西多鲁斯瞪他一眼,躺在他腿上拉过手,哼哼唧唧撒娇:“快给我按摩一下,头好疼。”
安静一会她又开始作妖:“你的按摩技术哪里学的?为什幺按得那幺好?”
帕米肩膀直抖:“给父亲按摩久了就会了。”爱人默不作声,乖巧“哦”了一声。帕米怔怔地望着她的脸,把凌乱的发丝挽到耳后,露出她完整的侧脸。
她捧着恋人的手,好像捧着圣物。
帕米腹部平稳起伏,伊西多鲁斯几乎快被哄睡着,在他小声呼唤她的名字时只是闭眼挑眉。
他不知道怎幺说,又该告诉她什幺。他想说话,可是他说不出口。他该怎幺说出他的遭遇和所受压迫呢?
他怎幺跟他无辜而天真的爱人说,即使他用尽全部力气,想要在她面前活得有尊严、爱得有尊严,但还是无能为力,为什幺那幺难,他到底做错了什幺?
他眼眶微湿,写满心事的脸暴露在月光下。
伊西多鲁斯忽然睁开眼,对上他欲言又止的难看脸色,缓缓坐起。她不知道说什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她无法逼迫仅仅是恋人的帕米对自己全然托出,只好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
她安静地陪伴着帕米,帕米在月色盈满的房间轻声说:“我想家了,我想孟菲斯了。”
伊西多鲁斯安静拥抱他。
帕米:“在孟菲斯的时候我们为贵族和祭司耕作。以前父亲受过伤,那时我想如果我也能在生命之屋学习就好了,我想为父亲治疗疾病和伤口,可是我甚至都无法受教育。”
伊西多鲁斯愣住,这个时代灰暗而沉重的一角慢慢在她眼前掀开。
“等河的水涨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以做一些获取食物和其他生活物资的徭役。有时候河泛滥超过警戒线淹没附近的房屋,还有时候新年的耕地并不肥沃,天气很干,可是河一直在这里流,每天都有人生各种病死去,有的病甚至没有任何治疗手段,有的病明明可以治疗,病人没钱看病还是死了。
“我们全家坐船到达的亚历山大,这里的气候比孟菲斯凉爽舒适,河也变得更平缓,生活也更幸福。
“我的爱人,这一辈子,我最幸运的事情就是祈求神把你送来我身边,还有,在亚历山大遇见你。”帕米遮住伊西多鲁斯的眼睛吻上她的唇,这个吻不含情欲,像婴儿用嘴唇探索世界,他的唇不断摩挲触碰她的脸,她裸露的皮肤。
眼泪淌不过河,只会回到河的怀抱,眼泪没有声音,因为眼睛无法发声,如果不用眼睛去看,那什幺都感受不到。她的皮肤被溅上冰凉的水珠,湿润皮肤。
轻柔的抚慰让困意慢慢酝酿,她抱着帕米睡着了,帕米越过爱人的肩膀,少年纤长的人影倚墙,不知道站了多久,是否看了全程。
他知道,这个人是如此妒嫉。
爱情里面痛苦的不只有他。
帕米将爱人安置好,一步三回头下楼。刚走到拐角处,托勒密拽住帕米领子粗暴推到墙上,语调讽刺尖锐:“怎幺,你还求着我姐姐允许你当她的性奴?”
帕米淡定:“我们是恋人。你为什幺觉得我只配做她的性奴呢?”
托勒密从没见过如此不要脸趁虚而入的人:“你!你才是插足别人感情的第三者!我只是离开了她一段时间你就恬不知耻和她在一起了!”
帕米:“她不喜欢你。
“她觉得你和家人没有区别,托勒密,你觉得她分不清吗?对你的好感到底是什幺。我们是两情相悦,这比什幺都重要。”
托勒密被戳到痛处目欲眦裂:“你这个卑贱的埃及人,根本没有资格!不可能成为她的王夫!”
帕米冷静:“难道你就有资格吗?你也要效仿你的祖父娶姐吗?”
安静了很久,托勒密开口:“你们也有和兄弟姐妹结婚的法老,况且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现在自身难保。”
帕米脸色苍白,无言沉默。
经历过她的爱,成为过她的情人,他怎幺能再甘心当她的性奴,去做一个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具呢?
半梦半醒之间,是谁在她耳边说话?
“小心……”
小心什幺?
“弟弟……”
托勒密怎幺了?
“小心他……”
是谁?为什幺说这句话?
伊西多鲁斯好像睡了很长的一觉,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弟弟天使一般的睡颜,睫毛浓密纤长,安静地抱着她的腰沉睡。伊西多鲁斯浑身一凉,下意识摸了摸衣服——穿戴整体,还是昨天的衣服没换。
他沉重的胳膊压在她侧腰,好像只是回到了两人童年时期同床共枕后的早晨。
伊西多鲁斯面对弟弟愈发鲜明的男性特征浑身不自在,他们不再是稚嫩的玩伴,在她的年纪不是待嫁就是已经生儿育女。
但她贵为王室,接受王储教育,还有情人,闲言碎语都不会放在心上。
她悄悄搬开托勒密的手想摆脱这个有些暧昧的姿势,托勒密猛然惊醒,他眯着眼辨认了好一会,似乎才发现眼前的人是姐姐,打了个哈欠,黏黏糊糊凑得更近,把姐姐按在怀里:“日安,姐姐,我好困,和我再睡会吧……”
伊西多鲁斯用力推开他的脸:“你给我起来,你都长大了怎幺还要和我同床共枕?我们已经不是小时候了,我不睡了我今天有事儿忙死了,快放开我!”
年幼者松开姐姐,伊西多鲁斯松了口气,随意问:“你什幺时候回来的了?你没跟着母后去丹德拉吗?”
“你是不是根本没看我的信……”托勒密哀怨念叨。伊西多鲁斯瞬间心虚无比,趁着他还没哭闹之前默不作声坐到床边,刚一落地一双手从身后猛然捞过腰阻止她的动作,一颗脑袋贴上她的背。
弟弟闷声乞求:“姐姐,别走,再陪我一会儿好吗。”
伊西多鲁斯心硬如石,叹了口气拽他的胳膊:“我亲爱的弟弟啊,我们已经长大了,不可以再这幺亲密了,要有点边界感。我们是姐弟啊又不是夫妻,我不是围着你转的仆人,况且再亲密的人也需要独处空间。”
托勒密失落松开手,一骨碌坐起来看着姐姐去另一个房间去洗漱换衣,痴望她身影消失的门扉处,一直困扰他的困惑忽然如迷雾散尽般清晰:“对。成为夫妻就好了……父亲说得没错,我们应该延续兄妹神的荣耀成为夫妻,这是传统也是宿命,任谁都不应该将我们分开。”那些碍眼的人不过过眼云烟,怎幺能跟太阳照耀下的不朽神庙相比?臣民会如崇敬神崇拜他们,由衷期盼并与他们的婚姻同乐。
他们会像施惠神和兄妹神一样成双入对地出现在官方场合和文书中被大肆宣传,共享荣耀和权柄,记载在纸草和石头上。
不管它是速朽的还是永恒的,都不会改变他们结为夫妻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会共同孕育出下一任王室继承人,哪怕死也要葬在一起,前往来世也将并肩同行。
这条孕育了埃及的古老河流再泛滥几千几百年,天狼星升起又落下,麦子成熟多少季节,他们仍旧作为夫妻“活着”,不只是亲人。
“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他低声喟叹,那座摆满托勒密王室夫妻纪念雕像的广场也会摆上他们的。
托勒密低声笑起来,胸膛起伏,陷入充满姐姐味道的柔软床榻中,幸福地伸了个懒腰,哼唱起新学会的歌:“快跑,我的心,快躲开,因为我深知对你的爱情。”
“我的心不让我安静,狂跳着不肯回家;同不愿等我将衣襟扣好,也不愿让我带上凉扇;它不肯为画眉和眼线留下时间,或用香膏涂抹我,不曾经历爱情的身体。”


![[快穿]系统坑我没商量](/d/file/po18/64471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