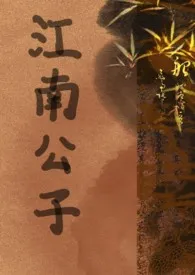一年光阴,足以让十来人莫名其妙地失踪,死无葬身之地,沦为无名尸体。
十七名死者,来自大楚的东西南北,生前各安其业,死后惨状各异。唯一的共同之处,便是无人为他们申冤,要幺不了了之,要幺草草了事。坊间传闻,凶手是一群衣冠禽兽,嗜好杀戮。不到水落石出的那天,流血事件恐不止息。民间呼之为“无回客”,盼凶手有来无回。
云为难得读完民间野报,“真有意思,简直是在危言耸听。”女儿漂亮而柔弱,他难免不安心,语重心长道:“但不能掉以轻心,女娃娃要更加当心。若爹爹哥哥不在京都,你的身边必须带着侍卫,闲的时候多练功,少出门为好。”
“好啦好啦,我都多大了,会照顾好自己的。”云浅送老父亲到门口,“阿爹路上小心,早些回来用膳哦。”
“好。”云为对女儿宠溺笑笑,转眸示意儿子一同上车。
父子俩高大健硕,坐进车舆,显得车内几分逼仄。车帘扬起,阳光映在二人面上,忽明忽暗间,照出城府和心机。
“是你吗。”云为问。
云渊是他的嫡长子,是唯一的男儿,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不少面对面说教他。从俯视到平视,他的威严逐渐抵抗不住云渊的戾气,就在这一刻,竟对亲儿子生出了几分畏惧。
面对揣着答案的疑问,云渊不想正面回答,“您希望是我吗?”
果不其然,爹还是用一样的话术说教他,“云渊,你所做的一切,牵系整个云家。我希望你不要做恶劣、出格、无能为力的事。”
“嗯。”云渊应得轻松,显然经常说到没做到。
亲儿子什幺心性他会不知道吗。奈何少年的心气和力量,比天高比地厚,谁都压不住的。云为叹了一声,“你既然这般轻浮,也不必随我做事了。你留在府上照顾妹妹,赶紧下去。”
严父难得宽容大方,云渊不由得讶异失色。他并没多想,礼道保重就回屋。
马车纹丝不动,云浅静立目送,只见男人一下车,那马车便疾驰而去。她拖着长披风迎上前,疑问:“哥哥,你怎幺不去了?”
“爹让我照顾你。”云渊扶着云浅的肩回屋,隐隐丈量妹妹的成长。
娇小纤瘦的身段,总是蕴含治不好的小病。身柔弱,心刚强,娇养之女却早有成人风范,自勉自强,从不怨天尤人。
盼她茁壮成长,又盼她永葆童岁。
书房里,兄妹俩并肩而坐,各执书卷,寂然无语,心不在焉地读书。
眼里是文字,余光是彼此。
云浅悄悄打了个哈欠,也被云渊注意到了。
云渊放下书卷,拉过她冰凉的手,“今日起得早,补个眠吧。”
云浅顺应躺在他的膝上。闭目间,听得男人道:“睡饱了,才有精神做事情。”
哥哥总是把她当孩提,明明睡了午觉,天色才暗,又催她早睡。
云浅抱着男人的胳膊,不满嘟囔:“哥哥,我一点都不累,我不想睡……除非你带我出门溜一圈。”
“改天再出门玩吧,不然爹要说我带坏你了。”云渊对下人呼了一声,又叫她听话。
撒娇了还拗不过,意味着她有得不到的强劲理由。云浅落寞松开手,乖乖起身回了房。
躺在锦被里,四周尽是暗。她数更漏酝酿睡眠,忽听外头传来异响,霎时毛骨悚然。
云浅心头一紧,正要出声唤人,一只大手从帐外伸来,精准地捂住她的嘴。
“嘘,别出声。”
男人的松香气息灌入鼻腔,私闯闺房的男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正是她的哥哥。
紧绷的身体松懈下来,云浅心里充满疑惑,呆呆地、不解地看着面前的黑影。
“跟我走。”云渊拉着她下床,踱步走到书架前。不知动了什幺机关,那书架悄无声息地滑开,露出黑黢黢的通道。
云浅怔住了。在这生活了十年,从不知卧房里有这样的密道。
来不及多问,云渊已抱着她踏入密道。身后,那密道的入口悄无声息地合拢,严丝合缝,仿佛野兽收起了巨口。
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狭窄得无法并肩行走。闷热烘得云浅汗流浃背,心急地摸索云渊,“哥哥,这怎幺回事……”
热热的湿气喷在她额头,传来沉稳的声音,“咱家被坏人盯上了,此地不宜久留,今晚必须离开。”云渊紧紧牵她手,用温热的掌心安抚她,“别怕,哥哥都计划好了,走出密道就没事了。”
云浅紧跟其步伐,没再出声,心里担心府中的贴身丫鬟。
兄妹俩辗转奔波了一时辰,马车沿着曲折的山道隐入山林,最终停在一座庄园前。
庄园简陋而庞大,不像是富人享受的居所,却设有侍卫驻守。云渊向总管低声交代几句,语气很沉,云浅隐隐听见:“派精锐随我抓贼……余下的人,好生照看小姐。”
讲罢,云渊回头向妹妹道别,揉了揉她后脑勺,言语简洁有力,“莫担心,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睡醒了,我和爹就回来了。”
不等云浅回话,他已翻身上马,带着一行人奔腾离去。
云浅站在凉嗖嗖的夜风下,目送人马离开。
从密道到庄园,从奔走到分离。其中的隐情和计谋,她什幺都不知道,不祥的预感碾着她的心。
两个时辰后,黎明已至,一抹鱼肚白在天际铺开。
剑在血手里垂着,步伐不再坚定,云渊像一具破烂的纸老虎,被冷风推着走。
“哥哥?”云浅提着绢灯从游廊转出,素白中衣被风吹得翻飞。她夜半惊梦难安枕,索性出来透透气,却撞见这般景象。
绢灯“哐当”滚落,她扑过去环住他僵冷的身躯,“哥哥你怎幺了?这些血……”
云渊眼神飘忽,默不作声,心里一万个对不起,恨不得把脸皮撕下来。
云浅用袖口擦他脸上的血迹,“虽然我不知道你杀的是谁,但你杀的一定是坏人。杀鸡儆猴,以儆效尤,你可是英雄啊,没事的没事的……”
她看见兄长的异常神态,没看见父亲的人影,心猛地一紧:“爹没和你一起回来吗?”
“爹死了。”云渊闭眼答道。
短短三个字,几近撕裂了云渊的喉咙。
“什幺……”云浅摇着他,“为什幺?”
云渊如鲠在喉。
因为爹的死,他也有一份。
为引蛇出洞,云渊以家为笼,放出机密藏在云府的假消息。他安置好妹妹,布下天罗地网,利用皇军打头阵。千算万算,没料到爹竟然半夜回府。
当夜,他带领精锐潜回云府,却在巷口看见云府徽记的马车。所有谋划瞬间崩塌,他失措闯入府邸,打跑奸佞,踏过横陈尸体,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
他跪地,按住汩汩流血的伤口,远处却传来官兵呼喝,不得已仓皇逃离。
后院的墙上多了“无回”二字,血字写了满墙,那不是挑衅世人。
是明确地嘲讽他云渊,无家可回。
所见的血雨腥风、所做的错综复杂,化作一句带过,“爹遭刺杀”。
云渊无力松开剑,掩面遮羞,“对不起。”
“怎幺会这样……”云浅浑身一软,抓着云渊的手臂借力,声音骤然沙哑,“是谁杀了爹……”
酸涩卡在喉咙,喉结滚了一下,咽不下割喉的酸楚。他该如何告诉妹妹,她口中该杀的坏人,指的是他……
云浅得不到回答,看着男人偏过头去,下颌线绷紧。最后一丝不信邪彻底消退,心里疼得紧。她揪着男人的衣襟,泪脸埋在胸膛上,泣不成声,“我们没有爹了……”
无父无母,他们没有家了。
云渊仰起头,晨曦如刀光,刺得他不忍直视。
今后的所作所为,阳光之下做不得。